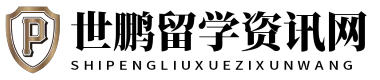让法律归法律。
冷静之余,最近的两起极端案例传递出来的迥异反应,却让我们思考另外一个话题:中国人的爱恨情仇观,到底向何处去?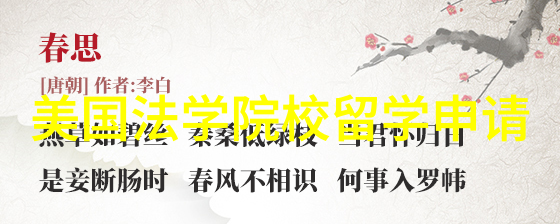
对于本案,相比于犯罪嫌疑人罗某的“尖子生”身份,被害人女儿在他班上的话更加感人。
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她说:我不恨他(罗某),一命抵一命没有用,希望他不再伤害别人。亲人被杀,这种略显平静的态度,很容易让人咀嚼出别样的滋味。
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,在留日学生江歌被杀案件中,作为母亲的江秋莲悲愤不已,对所谓“见死不救”的刘鑫“决不原谅”,并在网上发起“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”,目前征集人数超过150万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,姜木在失去心爱的女儿时的爱恨情仇是一个亲人最正常的表现。
所以,面对另一起凶案受害者女儿“我不恨凶手”的话语时,难免会有些不解,甚至难以接受。翻看网上评论,一位网友轻松成为导师:“你还年轻,你的大度有点‘是非’。可能你还没有从这次恶性事件中走出来,或者你还没有真正‘走进去’。你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失去父亲的滋味。对于肇事者来说,你还停留在‘同学’的印象里。善良是好事,但要注意是非尺度。
” 也许,在他眼里,为亲人被害而悲伤,为愤怒而憎恨,是一个是非问题,也是一个不能打折扣的原则问题。 但是,这位网友,以及持此观念的很多人,所不能理解的是,还有一种观念,叫作“不恨”;还有一种做法,叫作“宽恕”。已故学者于洪2007年写了一篇文章《有一种爱,我们还很陌生》,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
文中,余教授引用当年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园枪击案等事件,就中美两国民众对刑事案件的反应,做了对比和分析。“一个杀人犯开枪打死了32个人。凶手自己开枪了。
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燃了33根蜡烛,为33个生命祈祷。 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,‘当凶手在开枪的时候,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,但此时此刻,我相信上帝与他的灵魂同在,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。 ’” 其实1991年爱荷华大学卢刚事件也是如此。 这位留学美国的华人博士开枪射杀6人后,选择饮弹自绝。 艾奥瓦大学副校长安妮克莱里(Anne Clary)遇害后,她的亲属写信给卢刚的家人:“安妮最相信爱和宽恕。 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,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,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”,“在此时,比我们更悲痛的,只有你们一家。 请理解我们愿意和你分担这份悲伤。 ” 这些外国人所表达的原谅与和解,在中国的背景下是难以置信的。 或许,这种“爱”中,混同着宗教、文明等因素。 然而,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,根深蒂固的“爱”和“恨”的观念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本能。 现实中,江歌的母亲如此,亲人遇害后,在法院面前拉横幅、甚至要求判凶手死刑的人们,也是如此。这当然无可非议。
今天的我们,不必过于纠结究竟何种观念更加理性,更加优越,只是还要明白,“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。 “在尊重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,也要看到很多新生代的认知和心态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。 坚守自己的信念,不等于非得干预别人的想法。 不知道的,不了解的,不理解的,没必要一棍子打死。 诚然,年轻的罗某是犯罪嫌疑人,是涉嫌杀害老师的凶手,同时也是被害人孩子的同学,成绩优异的尖子生。 被害人女儿选择“不恨”,认为“一命抵一命没有用”,虽然让人不是滋味,却也是大实话:即便判处了凶手死刑,又怎能挽回逝者的生命? 此外,我国刑法明确规定,死刑不适用于18岁以下的人,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 “希望他不再伤害别人”,更体现了一位女孩的善良与希望,何错之有? 江歌杀人案,日本律师承认凶手最多被判20年监禁。 事实上,日本虽有死刑,却受到了严格限制。 据统计,从1991年到2015年的25年间,一审判决共判处死刑197人,平均每年不到8人,实际执行的就更少了。 被害人家属的恳求,并不能影响或者左右日本司法审判。中国是迄今为止保留死刑的国家,也是世界上死刑罪名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。
但是,死刑罪名也在明显减少。 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生效后,刑法中只有46个死刑罪名。 罪名条文的改革,死刑核准权的上收,勾勒出“少杀慎杀”的刑事政策新轮廓,与“私力救济”到“公力救济”一样,见证了文明的趋势。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。
从熟悉、面对和接受“不恨”开始,中国人的爱恨情仇观,或许也应该有一些改变。 虽然,这种“不讨厌”对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。